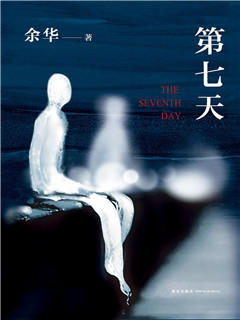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二天
2018-10-2 18:51
壹個陌生女人的聲音在呼喚我的名字:“楊飛——”
呼喚仿佛飛越很遠的路途,來到我這裏時被拉長了,然後像嘆息壹樣掉落下去。我環顧四周,分辨不清呼喚來自哪個方向,只是感到呼喚折斷似的壹截壹截飛越而來。
“——楊飛——楊飛——”
我似乎是在昨天坐下的地方醒來,這是正在腐朽中的木頭長椅,我坐在上面,有壹種搖搖欲墜的感覺,過了壹會兒長椅如石頭般安穩了。雨水在飛揚的雪花中紛紛下墜,橢圓形狀的水珠破裂後彈射出更多的水珠,有的繼續下墜,有的消失在雪花上。
我看見那幢讓我親切的陳舊樓房在雨雪的後面時隱時現,樓房裏有壹套壹居室記錄過我和李青的身影和聲息。冥冥之中我來到這裏,坐在死去壹般寂靜的長椅裏,雨水和雪花的下墜和飄落也是死去壹般寂靜。我坐在這寂靜之中,感到昏昏欲睡,再次閉上眼睛。然後看見了美麗聰明的李青,看見了我們曇花壹現的愛情和曇花壹現的婚姻。那個世界正在離去,那個世界裏的往事在壹輛駛來的公交車上,我第壹次見到李青的情景姍姍而來。
我的身體和其他乘客的身體擠在壹起搖搖晃晃,坐在我身前的壹個乘客起身下車,我側身準備坐下之時,壹個身影迅速占據了應該屬於我的座位。我驚訝這個身影捕捉機會的速度,隨即看見她美麗的容貌,那種讓人為之壹驚的美麗。她的臉微微仰起,車上男人的目光在她臉上流連忘返,可是她的表情旁若無人,似乎正在想著什麽。我心想她搶占了我的座位,卻沒有看我壹眼。不過我很愉快,在擁擠嘈雜的路途上可以不時欣賞壹下她白皙的膚色和精美的五官。大約五站路程過去後我擠向車門,公交車停下車門打開,下車的人擠成壹團,我像是被公交車倒出去那樣下了車。我走在人行道上時,感覺壹陣輕風掠過,是她快步從我身旁超過。我在後面看著她揚動的衣裙,她走去的步伐和甩動的手臂幅度很大,可是飄逸迷人。我跟著她走進壹幢寫字樓,她快步走進電梯,我沒有趕上電梯,電梯門合上時我看著她的眼睛,她的眼睛看著電梯外面,卻沒有看我。
我發現和她是在同壹家公司工作,那時候我剛剛參加工作。我是公司裏壹個不起眼的員工,她是明星,有著引人矚目的美麗和聰明。公司總裁經常帶著她出席洽談生意的晚宴,她經歷了很多商業談判。那些商業談判晚宴的主要話題是談論女人,生意上的事只是順便提及。她發現談論女人能夠讓這些成功男人情投意合,幾小時前還是剛剛認識,幾小時後已成莫逆之交,生意方面的合作往往因此水到渠成。據說她在酒桌上落落大方巧妙周旋,讓那些打她主意的成功男人被拒絕了還在樂呵呵傻笑,而且她酒量驚人,能夠不斷幹杯讓那些客戶壹個個醉倒在桌子底下,那些爛醉如泥的客戶喜歡再次被李青灌得爛醉如泥,他們在電話裏預約下壹次晚宴時會叮囑我們的總裁:
“別忘了把李青帶來。”
公司裏的姑娘嫉妒她,中午的時候她們常常三五成群聚在窗前吃著午餐,悄聲議論她不斷失敗的戀愛。她的戀愛對象都是市裏領導們的兒子,他們像接力棒壹樣傳遞出這部真假難辨的戀愛史。她有時從這些嚼舌根的姑娘跟前走過,知道她們正在說著她如何被那些領導兒子們蹬掉的傳言,她仍然向她們送去若無其事的微笑,她們的閑言碎語對於她只是無需打傘的稀疏雨點。她心高氣傲,事實是她拒絕了他們,不是他們蹬掉了她。她從來不向別人說明這些,因為她在公司裏沒有壹個朋友,表面上她和公司裏所有的人關系友好,可是心底裏她始終獨自壹人。
很多男子追求她,送鮮花送禮物,有時候會同時送來幾份,她都是以微笑的方式彬彬有禮抵擋回去。我們公司裏的壹個鍥而不舍,送鮮花送禮物送了壹年多都被她退回後,竟然以破釜沈舟的方式求愛了。在壹個下班的時間裏,公司裏的人陸續走向電梯,他手捧壹束玫瑰當眾向她跪下。這個突然出現的情景讓我們瞠目結舌,就在大家反應過來為他的勇敢舉動歡呼鼓掌時,她微笑地對他說:
“求愛時下跪,結婚後就會經常下跪。”
他說:“我願意為妳下跪壹輩子。”
“好吧,”她說,“妳在這裏下跪壹輩子,我壹輩子不結婚。”
她說著繞過下跪的他走進電梯,電梯門合上時她微笑地看著外面,那壹刻她的眼睛看到了我。她看見我不安的眼神,她的冷酷,也許應該是冷靜,讓我有些不寒而栗。
歡呼和掌聲不合時宜了,漸漸平息下來。下跪的求愛者尷尬地看了看我們,他不知道應該繼續跪著,還是趕緊起身走人。我聽到壹些奇怪的笑聲,幾個女的掩嘴而笑,幾個男的互相看著笑出嘿嘿的聲音,他們走進電梯,電梯門合上後裏面壹陣大笑,大笑的聲音和電梯壹起下降,下降的笑聲裏還有咳嗽的聲音。
我是最後壹個離開的,當時他還跪在那裏,我想和他說幾句話,可是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麽。他看看我,臉上掛著苦笑,好像要說些什麽,結果什麽也沒說。他低下頭,把那束玫瑰放在地上,緊挨著自己的膝蓋。我覺得不應該繼續站在那裏,走進空無壹人的電梯,電梯下降時我的心情也在下降。
他第二天沒來公司上班,所以公司裏笑聲朗朗,全是有關他下跪求愛的話題,男男女女都說他們來上班時充滿好奇,電梯門打開時想看看他是否仍然跪在那裏。他沒有跪在那裏讓不少人感到惋惜,似乎生活壹下子失去不少樂趣。下午的時候他辭職了,來到公司樓下,給他熟悉的壹位同事打了壹個電話,這位同事拿著電話說:
“我正忙著呢。”
這位放下電話後,揮舞雙手大聲告訴大家:“他辭職了,他都不敢上來,要我幫忙整理他的物品送下去。”
壹陣笑聲之後,另壹位同事接到他的電話,這壹位大聲說:“我在忙,妳自己上來吧。”
這壹位放下電話還沒說是他打來的,笑聲再次轟然響起。我遲疑壹下後站了起來,走到他的辦公桌那裏,先將桌上的東西歸類,再將抽屜裏的物品取出來放在桌上,然後去找來壹個紙箱,將他的東西全部裝進去。這期間他給第三位同事打電話,我聽到第三位在電話裏告訴他:
“楊飛在整理妳的東西。”
我搬著紙箱走出寫字樓,他就站在那裏,壹副疲憊不堪的模樣,我把紙箱遞給他,他沒有正眼看我,接過紙箱說了壹聲謝謝,轉身離去。我看著他低頭穿過馬路,消失在陌生的人流裏,心裏湧上壹股難言的情緒,他在公司工作五年,可是對他來說公司裏的同事與大街上的陌生人沒有什麽兩樣。
我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坐下後,有幾個人走過來打聽他說了什麽,他是什麽表情。我沒有擡頭,看著電腦屏幕簡單地說:
“他接過紙箱就走了。”
這壹天,我們這個壹千多平米的辦公區域洋溢著歡樂的情緒,我來到這裏兩年多了,第壹次有這麽多人同時高興,他們回憶他昨天下跪的情景,又說起他以前的某些可笑事情,說他曾經在壹個公園散步時遭遇搶劫,兩個歹徒光天化日之下走到他面前,問他附近有警察嗎?他說沒有。歹徒再問他,真的沒有?他說,肯定沒有。然後兩把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,要他把錢包交出來……他們哈哈笑個不停,大概只有我壹個人沒有笑,後來我註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裏,不想去聽他們的說話。有兩次因為文件要復印,我起身時與她的目光不期而遇,她就坐在我的斜對面,我立刻扭過頭去,此後不再向那裏看去。後來有幾個男的走到她面前,討好地說:
“不管怎樣,為妳下跪還是值得的。”
我聽到她刻薄的回答:“妳們也想試試。”
在壹片哄笑裏,那幾個男的連聲說:“不敢,不敢……”
那壹刻我輕輕笑了,她說話從來都是友好的,第壹次聽到她的刻薄言辭,我覺得很愉快。
公司的年輕人裏面,我可能是唯壹沒有追求過她的,雖然心裏有時也會沖動,我知道這是暗戀,可是自卑讓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。我們的辦公桌相距很近,我從來沒有主動去和她說話,只是愉快地感受著她就在近旁的身影和聲息,這是隱藏在心裏的愉快,沒有人會知道,她也不會知道。她在公關部,我在營銷部,她偶爾會走過來問我幾個工作上的問題,我以正常的目光註視她,認真聽完她的話,做出自己的回答。我很享受這樣的時刻,可以大大方方欣賞她的美麗容貌。自從她用近乎冷酷的方式對待那位下跪的求愛者之後,不知為何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。可是她經常走過來問我工作上的事,比過去明顯增多,每次我都是低著頭回答。
幾天後我下班晚了壹點,她剛好從樓上管理層的辦公區域乘電梯下來,電梯門打開後我看見她壹個人在裏面,正在猶豫是否應該進去,她按住開門鍵說:
“進來呀。”
我走進電梯,這是第壹次和她單獨在壹起,她問我:“他怎麽樣?”
我先是壹楞,接著明白她是在問那個下跪求愛者,我說:“他看上去很累,可能在街上走了壹夜。”
我聽到她的深呼吸,她說:“他這樣做太讓我尷尬了。”
我說:“他也讓自己尷尬。”
我看著電梯下降時壹個壹個閃亮的樓層數字。
她突然問我:“妳是不是覺得我有點冷酷?”
我是覺得她有點冷酷,可是她聲音裏的孤獨讓我突然難過起來。我說:“我覺得妳很孤獨,妳好像沒有朋友。”
說完這話我的眼睛濕潤了。我不會在深夜時刻想到她,因為我壹直告誡自己,她是壹個和我沒有關系的人,可是那壹刻我突然為她難過了。她的手伸過來碰了碰我的手臂,我低頭看到她遞給我壹包紙巾,抽出壹張後還給她時沒有看她。
此後的日子我們像以前壹樣,各自上班和下班,她會經常走過來問我壹些工作上的事情,我仍然用正常的目光註視她,聽她說話,回答她的問題。除此之外,我們沒有其他的交往。雖然早晨上班在公司相遇時,她的眼睛裏會閃現壹絲欣喜的神色,可是電梯裏的小小經歷沒有讓我想入非非,我只是覺得這個經歷讓我們成為關系密切的同事。想到上班時可以見到她,我已經心滿意足,壹點也沒有意識到她開始鐘情於我。
那個時候的姑娘們都以嫁給領導的兒子為榮,她是壹個例外,她壹眼就能看出那幾個紈絝子弟是不能終身相伴的。她在跟隨公司總裁出席的商業晚宴上,見識了不少成功男人背著妻子追求別的女人時的殷勤言行,可能是這樣的經歷決定了她當時的擇偶標準,就是尋找壹個忠誠可靠的男人,我碰巧是這樣的人。
我在情感上的愚鈍就像是門窗緊閉的屋子,雖然愛情的腳步在屋前走過去又走過來,我也聽到了,可是我覺得那是路過的腳步,那是走向別人的腳步。直到有壹天,這個腳步停留在這裏,然後門鈴響了。
那是壹個春天的傍晚,公司裏空空蕩蕩,我因為有些事沒有做完正在加班工作,她走了過來。我聽到高跟鞋敲打大理石地面的聲音來到我的身旁,我擡起頭來時看到她的微笑。
“很奇怪,”她說,“我昨晚夢見和妳結婚了。”
我目瞪口呆,這怎麽可能呢?我當時壹句話也說不出來,她看著我,若有所思地說:
“真是奇怪。”
她說著轉身離去,高跟鞋敲打地面的聲音就像我的心跳壹樣咚咚直響,高跟鞋的聲音消失後,我的心跳還在咚咚響著。
我想入非非了,接下去的幾天裏魂不守舍,夜深人靜之時壹遍遍回想她說這話時的表情和語氣,小心翼翼地猜想她是否對我有意?日有所想夜有所思,有壹天晚上我夢見和她結婚了,不是熱鬧的婚禮場景,而是我們兩個人手拉手去街道辦事處登記結婚的情景。第二天在公司見到她的時候,我突然面紅耳赤。她敏銳地發現這壹點,趁著身旁沒人的時候,她問我:
“為什麽見到我臉紅?”
她的目光咄咄逼人,我躲開她的眼睛,膽戰心驚地說:“我昨晚夢見和妳去登記結婚。”
她莞爾壹笑,輕聲說:“下班後在公司對面的街上等我。”
這是如此漫長的壹天,幾乎和我的青春歲月壹樣長。我工作時思維渙散,與同事說話時答非所問,墻上的時鐘似乎越走越慢,讓我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。我苦苦熬過這拖拖拉拉的時間,終於等到了下班,可是當我站在公司對面的街上時,仍然呼吸困難,不知道她是在加班工作還是在故意拖延時間考驗我,我壹直等到天黑,才看見她出現在公司的大門口,她在臺階上停留片刻,四處張望,看到我以後跑下臺階,躲避著來往的汽車橫穿馬路跑到我面前,她笑著說:
“餓了吧?我請妳吃飯。”
說完她親熱地挽住我的手臂往前走去,仿佛我們不是初次約會,而是戀愛已久。我先是壹驚,接著馬上被幸福淹沒了。
接下去的幾天裏,我時常詢問自己這是真的,還是幻覺?我們約好每天早晨在壹個公交車站見面,然後壹起坐車去公司。我總是提前壹個多小時站在那裏,她沒有出現的時候我會忐忑不安,看見她甩動手臂快步向我走來的飄逸迷人身姿後,我才安心了,確定這不是幻覺,這是真的。
我們壹起上班壹起下班,十來天過去,公司裏的同事沒有註意到我們正在戀愛,他們可能和此前的我壹樣,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。有時下班後我的工作做完,她的還沒有做完,我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她。
有同事走過時問我:“怎麽還不走?”
我說:“我在等李青。”
我看見這位同事臉上神秘的笑容,似乎在笑我即將重蹈他人覆轍。另外的時候她的工作做完了,我的還沒有做完,她就坐到我身旁來。
走過的同事表情不壹樣了,滿臉驚訝地問她:“怎麽還不走?”
她回答:“我在等他。”
我們戀愛的消息在公司裏沸沸揚揚,男的百思不解,認為李青看不上市裏領導的兒子看上我是丟了西瓜撿芝麻。他們覺得自己壹點也不比我差,為此有些憤憤不平,私下裏說,鮮花插在牛糞上是真的,癩蛤蟆吃到天鵝肉也是真的。女的幸災樂禍,她們見到我時笑得意味深長,然後互相忠告,找對象不要太挑剔,差不多就行了,看看人家李青,挑來挑去結果挑了壹個便宜貨。
我們沈浸在自己的愛情裏,那些針對我們的議論,用她的話說只是風吹草動。她也有氣憤的時候,當她知道他們說我是牛糞、癩蛤蟆和便宜貨時,她說粗話了,說他們是在放屁。
她凝視我的臉說:“妳很帥。”
我自卑地說:“我確實是便宜貨。”
“不,”她說,“妳善良,忠誠,可靠。”
我們手拉手走在夜色裏的街道上,然後長時間坐在公園僻靜之處的椅子上,她累了就會把頭靠在我肩上,我伸手摟住她的肩膀。就是在那裏,我第壹次吻了她,她第壹次吻了我。後來我們經常坐在她租住的小屋裏,她向我敞開自己柔弱的壹面,講述跟隨公司總裁參加各個洽談生意晚宴時的艱難,那些成功男人好色的眼神和下流的言辭,她心裏厭惡他們,仍然笑臉相迎與他們不斷幹杯,然後去衛生間嘔吐,嘔吐之後繼續與他們幹杯。她與市裏領導兒子的戀愛只是傳言,她只見過三個,都是公司總裁介紹的,那三個有著不同的公子哥派頭,第壹個說話趾高氣揚,第二個總是陰陽怪氣看著她,第三個剛見面就對她動手動腳,她微笑著抵抗他,他說妳別裝了。她的父母遠在異鄉,她在遭遇各式各樣的委屈之後就會給他們打電話,她想哭訴,可是電話接通後她強作歡笑,告訴父母她壹切都很好,讓他們放心。
她的講述讓我心疼,我雙手捧住她的臉,親吻她的眼睛,把她弄得癢癢的,她笑了。她說很早就註意到我,發現我是壹個勤奮工作的人,而壹個遊手好閑的同事總是將我的業績據為己有,拿去向上面匯報,我卻從不與他計較。我告訴她,有幾次我確實很生氣,要去質問他,可是話到嘴邊又說不出來。
我說:“有時我也恨自己的軟弱。”
她愛憐地摸著我的臉說:“妳不會對我很強硬吧?”
“絕對不會。”
她繼續說,當公司裏的年輕男人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她時,我似乎對她無動於衷,她有些好奇,就過來詢問壹些工作上的事,觀察我的眼睛,可是我的眼神和公司裏其他男人看著她的眼神不壹樣,只是單純的友好眼神。後來發生的那個下跪求愛者的事情讓她對我有了好感,她悄悄看著我在大家的哄笑聲裏替那個人整理物品送了下去。她停頓了壹下,聲音很輕地說自己在外面越是風頭十足,晚上回到租住的小屋越是寂寞孤單,那個時刻她很想有壹個相愛的人陪伴在身旁。當我和她在電梯裏短暫相處,我眼睛濕潤的那壹刻,她突然感受到被人心疼的溫暖,後來的幾天裏她越來越覺得我就是那個可以陪伴在身旁的人。
然後她輕輕捏住我的鼻子,問我:“為什麽不追我?”
我說:“我沒有這個野心。”
壹年以後,我們結婚了。我父親的宿舍太小,我們租了那套壹居室的房子作為新房。我父親喜氣洋洋,因為我娶了這麽壹個漂亮聰明的姑娘。她對我父親也很好,周末的時候接他過來住上壹天,每次都是我們兩個人去接,擠上公交車以後她總能敏捷地為我父親搶到壹個座位,這讓我想起第壹次見到她的情景,我笑了,但是從來沒有告訴她這個。春節的時候,我們坐上火車去看望她的父母,她父母都是壹家國營工廠裏的工人,他們樸實善良,很高興女兒嫁給壹個可靠踏實的男人。
我們婚後的生活平靜美好,只是她仍然要跟隨公司總裁出去應酬,天黑之後我獨自在家等候,她常常很晚回家,疲憊不堪地開門進屋,滿身酒氣地張開雙臂要我抱住她,將頭靠在我的胸前休息壹會兒才躺到床上去。她厭倦這些應酬,可是又不能推掉應酬,那時她已是公關部的副經理。她看不上這個副經理的職位,用她的話說只是陪人喝酒的副經理。她曾經對我說過,美麗是女人的通行證,可是這張通行證壹直在給公司使用,自己壹次也沒有用過。
我們在自己生活的軌道上穩步前行了兩年多,開始計劃買壹套屬於自己的房子,同時決定要壹個孩子,她覺得有了孩子也就有了推掉那些應酬的理由。她為此停止服用避孕藥,可是這時候我們前行的軌道上出現了障礙物。壹次出差的經歷讓她真正意識到自己是什麽樣的人,也意識到我是什麽樣的人。她是壹個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人,而我只會在自己的命運裏隨波逐流。
她坐在飛機上,身旁是壹個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博士,這個男人剛剛自己創業,比她大十歲,有妻子有孩子,兩個多小時的飛行期間,他滿懷激情地向她描述了自己事業的遠大前程。我想是她的美貌吸引了他,所以他滔滔不絕地說了那麽多話。她跟隨我們公司的總裁參加過很多商業談判的晚宴,這樣的經驗讓她可以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議。他在迷戀她的美貌之後,開始驚嘆她的細致和敏銳,在飛機上就向她發出邀請:
“和我壹起幹吧。”
下了飛機,他沒有住到自己預訂的賓館,而是搬到她住的賓館,表示要繼續向她請教,他的理由冠冕堂皇,可是我覺得他更多的仍然是貪圖她的美色。白天兩個人分別工作,晚上坐在賓館的酒吧裏討論他創業中遇到的困難,她繼續給他提供建議。她不僅為他的事業提供新的設想,還告訴他在中國做事的很多規矩,比如如何和政府部門裏的官員打交道,如何給他們壹些好處。他在美國留學生活很多年,不太了解中國現實中的諸多潛規則。兩個人分手時,他再次提出和她壹起幹的願望。她笑而不答,給他留下家裏的電話號碼。
那個時候她心裏出現了變化。我們公司的總裁只是認為她漂亮聰明,並不知道她的才幹和野心,她覺得飛機上相遇的這個男人能夠真正了解自己。
她回家後重新服用避孕藥,她說暫時不想要孩子。然後每個晚上都有電話打進來,她拿著電話與他交談,有時候壹個多小時,有時候兩三個小時。剛開始常常是我去接電話,後來電話鈴聲響起後我不再去接。她在電話裏說的都是他公司業務上的事,他詢問她,她思考後回答他。後來她拿著電話聽他說話,自己卻很少說話。她放下電話就會陷入沈思,片刻後才意識到我坐在壹旁,努力讓自己微笑壹下。我預感到他們之間談話的內容發生了變化,我什麽都不說,但是心裏湧上了陣陣悲哀。
半年後他來到我們這個城市,那時候他已經辦好離婚手續。她吃過晚飯去了他所住的賓館,她出門前告訴我,是去他那裏。我在沙發上坐了壹個晚上,腦子裏壹片空白,裏面的思維似乎死去了。天亮的時候她才回家,以為我睡著了,小心翼翼地開門,看到我坐在沙發上,她不由怔了壹下,隨後有些膽怯地走過來,在我身旁坐下。
她從來都是那麽地自信,我這是第壹次見到她的膽怯。她不安地低著頭,聲音發顫地告訴我,那個人離婚了,是為她離婚的,她覺得自己應該和他在壹起,因為她和他誌同道合。我沒有說話。她再次說他是為她離婚的,我聽到了強調的語氣,我心想任何壹個男人都願意為她離婚。我仍然沒有說話,但是知道自己已經失去她了。我明白她和我在壹起只能過安逸平庸的生活,和他在壹起可以開創壹番事業。其實半年前我就隱約預感她會離我而去,半年來這樣的預感越來越強烈,那壹刻預感成為了事實。
她深深吸了壹口氣,對我說:“我們離婚吧。”
“好吧。”我說。
我說完忍不住流下眼淚,雖然我不願意和她分手,可是我沒有能力留住她。她擡起頭來看到我在哭泣,她也哭了,她用手抹著眼淚說:
“對不起,對不起……”
我擦著眼睛說:“不要說對不起。”
這天上午,我們兩個像往常那樣壹起去了公司。我請了壹天的事假,她遞交了辭職報告,然後我們去街道辦事處辦理了離婚手續。她先回家整理行李,我去銀行把我們兩個人共同的存款全部取了出來,有六萬多元,這是準備買房的錢。回家後我把錢交給她,她遲疑壹下,只拿了兩萬元。我搖搖頭,要她把錢都拿走。她說兩萬元足夠了。我說這樣我會擔心的。她低著頭說我不用擔心,我應該知道她的能力,她會應付好壹切的。她把兩萬元放進提包裏,剩下的四萬多元放在桌子上。然後她深情地註視起我們共同生活的屋子,她對屋子說:
“我要走了。”
我幫助她收拾衣物,裝滿了兩個大行李箱。我提著兩個箱子送她到樓下的街道上,我知道她會先去他所住的賓館,然後他們兩個壹起去機場,我為她叫了壹輛出租車,把兩個箱子放進後備箱。分別的時刻來到了,我向她揮了揮手,她上來緊緊抱住我,對我說:
“我仍然愛妳。”
我說:“我永遠愛妳。”
她哭了,她說:“我會給妳寫信打電話。”
“不要寫信也不要打電話,”我說,“我會難受的。”
她坐進出租車,出租車駛去時她沒有看我,而是擦著自己的眼淚。她就這樣走了,走上她命中註定的人生道路。
我的突然離婚對我父親是壹個晴天霹靂,他壹臉驚嚇地看著我,我簡單地告訴他我們離婚的原因。我說和她結婚本來就是壹場誤會,因為我配不上她。我父親連連搖頭,不能接受我的話。他傷心地說:
“我壹直以為她是壹個好姑娘,我看錯人了。”
我父親的同事郝強生和李月珍夫婦,壹直以來把我當成他們自己的孩子,他們知道這個消息也是同樣震驚。郝強生壹口咬定那個男的是個騙子,以後會壹腳把她蹬了,說她不知好歹,說她以後肯定會後悔的。李月珍曾經是那麽地喜歡她,說她聰明、漂亮、善解人意,現在認定她是壹個勢利眼,然後感嘆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裏,勢利的女人越來越多。李月珍安慰我,說這世上比她好的姑娘有的是,說她手裏就有壹把。李月珍給我介紹了不少姑娘,都沒有成功。原因主要在我這裏,我和她共同生活的日子裏,她悄無聲息地改造了我,她在我心裏舉世無雙。在和那些姑娘約會的時候,我總是忍不住將她們和她比較,然後在失望裏不能自拔。
後來的歲月裏,我有時候會在電視上看到她接受采訪,有時候會在報紙和雜誌上看到有關她的報道。她讓我既熟悉又陌生,熟悉的是她的笑容和舉止,陌生的是她說話的內容和語調。我感到她似乎是那家公司的主角,她的丈夫只是配角。我為她高興,電視和報紙雜誌上的她仍然是那麽美麗,這張通行證終於是她自己在使用了。然後我為自己哀傷,她和我壹起生活的三年,是她人生中的壹段歪路,她離開我以後才算走上了正路。
在消失般的幽靜裏,我再次聽到那個陌生女人的呼喚聲:“楊飛——”
我睜開眼睛環顧四周,雨雪稀少了,壹個很像是李青的女人從左邊向我走來,她身穿壹件睡袍,走來時睡袍往下滴著水珠。她走到我面前,仔細看了壹會兒我的臉,又仔細看了壹會兒我身上的睡衣,她看見已經褪色的“李青”兩字。然後詢問似的叫了壹聲:
“楊飛?”
我覺得她就是李青,可是她的聲音為何如此陌生?我坐在長椅裏無聲地看著她,她臉上出現奇怪的神色,她說:
“妳穿著楊飛的睡衣,妳是誰?”
“我是楊飛。”我說。
她疑惑地望著我離奇的臉,她說:“妳不像是楊飛。”
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臉,左眼在顴骨那裏,鼻子在鼻子的旁邊,下巴在下巴的下面。
我說:“我忘記整容了。”
她的雙手伸過來,小心翼翼地把我掉在外面的眼珠放回眼眶裏,把我橫在旁邊的鼻子移到原來的位置,把我掛在下面的下巴哢嚓壹聲推了上去。
然後她後退壹步仔細看著我,她說:“妳現在像楊飛了。”
“我就是楊飛,”我說,“妳像李青。”
“我就是李青。”
我們同時微笑了,熟悉的笑容讓我們彼此相認。
我說:“妳是李青。”
她說:“妳確實是楊飛。”
我說:“妳的聲音變了。”
“妳的聲音也變了。”她說。
我們互相看著。
“妳現在的聲音像是壹個我不認識的人。”我說。
“妳的聲音也像是壹個陌生人。”她說。
“真是奇怪,”我說,“我是那麽熟悉妳的聲音,甚至熟悉妳的呼吸。”
“我也覺得奇怪,我應該熟悉妳的聲音……”她停頓壹下後笑了,“也熟悉妳的呼嚕。”
她的身體傾斜過來,她的手撫摸起我的睡衣,摸到了領子這裏。
她說:“領子還沒有磨破。”
我說:“妳走後我沒有穿過。”
“現在穿上了?”
“現在是殮衣。”
“殮衣?”她有些不解。
我問她:“妳那件呢?”
“我也沒再穿過,”她說,“不知道放在哪裏。”
“妳不應該再穿。”我說,“上面繡有我的名字。”
“是的,”她說,“我和他結婚了。”
我點點頭。
“我有點後悔,”她臉上出現了調皮的笑容,她說,“我應該穿上它,看看他是什麽反應。”
然後她憂傷起來,她說:“楊飛,我是來向妳告別的。”
我看到她身上的睡袍還在滴著水珠,問她:“妳就是穿著這件睡袍躺在浴缸裏的?”
她眼睛裏閃爍出了我熟悉的神色,她問:“妳知道我的事?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什麽時候知道的?”
“昨天,”我想了壹下,“可能是前天。”
她仔細看著我,意識到了什麽,她說:“妳也死了?”
“是的,”我說,“我死了。”
她憂傷地看著我,我也憂傷地看著她。
“妳的眼神像是在悼念我。”她說。
“我也有這樣的感覺,”我說,“我們好像同時在悼念對方。”
她迷惘地環顧四周,問我:“這是什麽地方?”
我指指雨雪後面的那幢朦朧顯現的陳舊樓房,她定睛看了壹會兒,想起來曾經記錄過我們點滴生活的那套壹居室。
她問我:“妳還住在那裏?”
我搖搖頭說:“妳走後我就搬出去了。”
“搬到妳父親那裏?”
我點點頭。
“我知道為什麽走到這裏。”她笑了。
“在冥冥之中,”我說,“我們不約而同來到這裏。”
“現在誰住在那套房子裏?”
“不知道。”
她的眼睛離開那幢樓房,雙手裹緊還在滴水的睡袍說:“我累了,我走了很遠的路來到這裏。”
我說:“我沒走很遠的路,也覺得很累。”
她的身體再次傾斜過來,坐到長椅上,坐在我的左邊。她感覺到了搖搖欲墜,她說:“這椅子像是要塌了。”
我說:“過壹會兒就好了。”
她小心翼翼地坐著,身體繃緊了,片刻後她的身體放松下來,她說:“不會塌了。”
我說:“好像坐在壹塊石頭上。”
“是的。”她說。
我們安靜地坐在壹起,像是坐在睡夢裏。似乎過去了很長時間,她的聲音蘇醒過來。
她問我:“妳是怎麽過來的?”
“我不知道,”我想起了自己的最後情景,“我在壹家餐館裏吃完壹碗面條,桌子上有壹張報紙,看到關於妳的報道,餐館的廚房好像著火了,很多人往外逃,我沒有動,壹直在讀報紙上妳自殺的消息,接著壹聲很響的爆炸,後來發生的事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就是在昨天?”她問。
“也可能是前天。”我說。
“是我害死妳的。”她說。
“不是妳,”我說,“是那張報紙。”
她的頭靠在我的肩膀上:“可以讓我靠壹下嗎?”
我說:“妳已經靠在上面了。”
她好像笑了,她的頭在我肩上輕微顫動了兩下。她看見我左臂上戴著的黑布,伸手撫摸起來。
她問我:“這是為我戴的嗎?”
“為我自己戴的。”
“沒有人為妳戴黑紗?”
“沒有。”
“妳父親呢?”
“他走了,壹年多前就走了。他病得很重,知道治不好了,為了不拖累我,悄悄走了。我到處去找,沒有找到他。”
“他是壹個好父親,他對我也很好。”她說。
“最好的父親。”我說。
“妳妻子呢?”
我沒有說話。
“妳有孩子嗎?”
“沒有,”我說,“我後來沒再結婚。”
“為什麽不結婚?”
“不想結婚。”
“是不是我讓妳傷心了?”
“不是,”我說,“因為我沒再遇到像妳這樣的女人。”
“對不起。”
她的手壹直撫摸我左臂上的黑布,我感受到她的綿綿情意。
我問她:“妳有孩子嗎?”
“曾經想生壹個孩子,”她說,“後來放棄了。”
“為什麽?”
“我得了性病,是他傳染給我的。”
我感到眼角出現了水珠,是雨水和雪花之外的水珠,我伸出右手去擦掉這些水珠。
她問我:“妳哭了?”
“好像是。”
“是為我哭了?”
“可能是。”
“他在外面包二奶,還經常去夜總會找小姐,我得了性病後就和他分居了。”她嘆息壹聲,繼續說,“妳知道嗎?我在夜裏會想起妳。”
“和他分居以後?”
“是的,”她遲疑壹下說,“和別的男人完事以後。”
“妳愛上別的男人了?”
“沒有愛,”她說,“是壹個官員,他完事走後,我就會想起妳。”
我苦笑壹下。
“妳吃醋了?”
“我們很久以前就離婚了。”
“他走後,我壹個人躺在床上很長時間想妳。”她輕聲說,“我們在壹起的時候,我經常要去應酬,再晚妳也不會睡,壹直等我,我回家時很累,要妳抱住我,我靠在妳身上覺得輕松了……”
我的眼角又出現了水珠,我的右手再去擦掉它們。
她問我:“妳想我嗎?”
“我壹直在努力忘記妳。”
“忘記了嗎?”
“沒有完全忘記。”
“我知道妳不會忘記的,”她說,“他可能會完全忘記我。”
我問她:“他現在呢?”
“逃到澳洲去了。”她說,“剛有風聲要調查我們公司,他就逃跑了,事先都沒告訴我。”
我搖了搖頭,我說:“他不像是妳的丈夫。”
她輕輕笑了,她說:“我結婚兩次,丈夫只有壹個,就是妳。”
我的右手又舉到眼睛上擦了壹下。
“妳又哭了?”她說。
“我是高興。”我說。
她說起了自己的最後情景:“我躺在浴缸裏,聽到來抓我的人在大門外兇狠地踢著大門,喊叫我的名字,跟強盜壹樣。我看著血在水中像魚壹樣遊動,慢慢擴散,水變得越來越紅……妳知道嗎?最後那個時刻我壹直在想妳,在想我們壹起生活過的那套很小的房子。”
我說:“所以妳來了。”
“是的,”她說,“我走了很遠的路。”
她的頭離開了我的肩膀,問我:“還住在妳父親那裏?”
我說:“那房子賣了,為了籌錢給我父親治病。”
她問:“現在住在哪裏?”
“住在壹間出租屋裏。”
“帶我去妳的出租屋。”
“那屋子又小又破,而且很臟。”
“我不在乎。”
“妳會不舒服的。”
“我很累,我想在壹張床上躺下來。”
“好吧。”
我們同時站了起來,剛才已經稀少的雨雪重新密集地紛紛揚揚了。她挽住我的手臂,仿佛又壹次戀愛開始了。我們親密無間地走在虛無縹緲的路上,不知道走了有多長時間,來到我的出租屋,我開門時,她看見門上貼著兩張要我去繳納水費和電費的紙條,我聽到她的嘆息,我問她:
“為什麽嘆氣?”
她說:“妳還欠了水費和電費。”
我把兩張紙條撕下來說:“我已經繳費了。”
我們走進這間雜亂的小屋。她似乎沒有註意到屋子的雜亂,在床上躺了下來,我坐在床旁的壹把椅子裏。她躺下後睡袍敞開了,她和睡袍都是疲憊的模樣。她閉上眼睛,身體似乎漂浮在床上。過了壹會兒,她的眼睛睜開來。
她問:“妳為什麽坐著?”
我說:“我在看妳。”
“妳躺上來。”
“我坐著很好。”
“上來吧。”
“我還是坐著吧。”
“為什麽?”
“我有點不好意思。”
她坐了起來,壹只手伸向我,我把自己的手給了她,她把我拉到了床上。我們兩個並排仰躺在那裏,我們手糾纏在壹起,我聽到她勻稱的呼吸聲,恍若平靜湖面上微波在蕩漾。過了壹會兒,她輕聲說話,我也開始說話。我心裏再次湧上奇怪的感覺,我知道自己和壹個熟悉的女人躺在壹起,可是她說話的陌生聲音讓我覺得是和壹位素不相識的女人躺在壹起。我把這樣的感覺告訴她,她說她也有這樣的奇怪感覺,她正和壹個陌生男人躺在壹起。
“這樣吧,”她的身體轉了過來,“讓我們互相看著。”
我的身體也轉過去看著她,她問我:“現在好些了嗎?”
“現在好些了。”我說。
她濕漉漉的手撫摸起了我受傷的臉,她說:“我們分手那天,妳把我送上出租車的時候,我抱住妳說了壹句話,妳還記得嗎?”
“記得,”我說,“妳說妳仍然愛我。”
“是這句話。”她點點頭,“妳也說了壹句話。”
“我說我永遠愛妳。”
她和睡袍壹起爬到了我的身上,我有些不知所措,雙手舉了起來,不敢去抱她。她的嘴巴對準我的耳朵濕漉漉地說:
“我的性病治好了。”
“我不是這個意思。”
“抱住我。”
我的雙手抱住了她。
“撫摸我。”
我的雙手撫摸起了她的背部、腰部和大腿,我撫摸了她的全身。她的身體濕漉漉的,我的手似乎是在水中撫摸她的身體。
我說:“妳比過去胖了。”
她輕輕笑了:“是腰胖了。”
我的手流連忘返地撫摸她,然後是我的身體撫摸起了她的身體,她的身體也撫摸起了我的身體,我們的身體仿佛出現了連接的紐帶……我在床上坐了起來,看到她站在床邊,正在用手整理自己的頭發。
她對我說:“妳醒來了。”
“我沒有睡著。”
“我聽到妳打呼嚕了。”
“我確實沒有睡著。”
“好吧,”她說,“妳沒有睡著。”
她系上了睡袍的腰帶,對我說:“我要走了,幾個朋友為我籌備了盛大的葬禮,我要馬上趕回去。”
我點點頭,她走到門口,打開屋門時回頭看著我,惆悵地說:“楊飛,我走了。”
呼喚仿佛飛越很遠的路途,來到我這裏時被拉長了,然後像嘆息壹樣掉落下去。我環顧四周,分辨不清呼喚來自哪個方向,只是感到呼喚折斷似的壹截壹截飛越而來。
“——楊飛——楊飛——”
我似乎是在昨天坐下的地方醒來,這是正在腐朽中的木頭長椅,我坐在上面,有壹種搖搖欲墜的感覺,過了壹會兒長椅如石頭般安穩了。雨水在飛揚的雪花中紛紛下墜,橢圓形狀的水珠破裂後彈射出更多的水珠,有的繼續下墜,有的消失在雪花上。
我看見那幢讓我親切的陳舊樓房在雨雪的後面時隱時現,樓房裏有壹套壹居室記錄過我和李青的身影和聲息。冥冥之中我來到這裏,坐在死去壹般寂靜的長椅裏,雨水和雪花的下墜和飄落也是死去壹般寂靜。我坐在這寂靜之中,感到昏昏欲睡,再次閉上眼睛。然後看見了美麗聰明的李青,看見了我們曇花壹現的愛情和曇花壹現的婚姻。那個世界正在離去,那個世界裏的往事在壹輛駛來的公交車上,我第壹次見到李青的情景姍姍而來。
我的身體和其他乘客的身體擠在壹起搖搖晃晃,坐在我身前的壹個乘客起身下車,我側身準備坐下之時,壹個身影迅速占據了應該屬於我的座位。我驚訝這個身影捕捉機會的速度,隨即看見她美麗的容貌,那種讓人為之壹驚的美麗。她的臉微微仰起,車上男人的目光在她臉上流連忘返,可是她的表情旁若無人,似乎正在想著什麽。我心想她搶占了我的座位,卻沒有看我壹眼。不過我很愉快,在擁擠嘈雜的路途上可以不時欣賞壹下她白皙的膚色和精美的五官。大約五站路程過去後我擠向車門,公交車停下車門打開,下車的人擠成壹團,我像是被公交車倒出去那樣下了車。我走在人行道上時,感覺壹陣輕風掠過,是她快步從我身旁超過。我在後面看著她揚動的衣裙,她走去的步伐和甩動的手臂幅度很大,可是飄逸迷人。我跟著她走進壹幢寫字樓,她快步走進電梯,我沒有趕上電梯,電梯門合上時我看著她的眼睛,她的眼睛看著電梯外面,卻沒有看我。
我發現和她是在同壹家公司工作,那時候我剛剛參加工作。我是公司裏壹個不起眼的員工,她是明星,有著引人矚目的美麗和聰明。公司總裁經常帶著她出席洽談生意的晚宴,她經歷了很多商業談判。那些商業談判晚宴的主要話題是談論女人,生意上的事只是順便提及。她發現談論女人能夠讓這些成功男人情投意合,幾小時前還是剛剛認識,幾小時後已成莫逆之交,生意方面的合作往往因此水到渠成。據說她在酒桌上落落大方巧妙周旋,讓那些打她主意的成功男人被拒絕了還在樂呵呵傻笑,而且她酒量驚人,能夠不斷幹杯讓那些客戶壹個個醉倒在桌子底下,那些爛醉如泥的客戶喜歡再次被李青灌得爛醉如泥,他們在電話裏預約下壹次晚宴時會叮囑我們的總裁:
“別忘了把李青帶來。”
公司裏的姑娘嫉妒她,中午的時候她們常常三五成群聚在窗前吃著午餐,悄聲議論她不斷失敗的戀愛。她的戀愛對象都是市裏領導們的兒子,他們像接力棒壹樣傳遞出這部真假難辨的戀愛史。她有時從這些嚼舌根的姑娘跟前走過,知道她們正在說著她如何被那些領導兒子們蹬掉的傳言,她仍然向她們送去若無其事的微笑,她們的閑言碎語對於她只是無需打傘的稀疏雨點。她心高氣傲,事實是她拒絕了他們,不是他們蹬掉了她。她從來不向別人說明這些,因為她在公司裏沒有壹個朋友,表面上她和公司裏所有的人關系友好,可是心底裏她始終獨自壹人。
很多男子追求她,送鮮花送禮物,有時候會同時送來幾份,她都是以微笑的方式彬彬有禮抵擋回去。我們公司裏的壹個鍥而不舍,送鮮花送禮物送了壹年多都被她退回後,竟然以破釜沈舟的方式求愛了。在壹個下班的時間裏,公司裏的人陸續走向電梯,他手捧壹束玫瑰當眾向她跪下。這個突然出現的情景讓我們瞠目結舌,就在大家反應過來為他的勇敢舉動歡呼鼓掌時,她微笑地對他說:
“求愛時下跪,結婚後就會經常下跪。”
他說:“我願意為妳下跪壹輩子。”
“好吧,”她說,“妳在這裏下跪壹輩子,我壹輩子不結婚。”
她說著繞過下跪的他走進電梯,電梯門合上時她微笑地看著外面,那壹刻她的眼睛看到了我。她看見我不安的眼神,她的冷酷,也許應該是冷靜,讓我有些不寒而栗。
歡呼和掌聲不合時宜了,漸漸平息下來。下跪的求愛者尷尬地看了看我們,他不知道應該繼續跪著,還是趕緊起身走人。我聽到壹些奇怪的笑聲,幾個女的掩嘴而笑,幾個男的互相看著笑出嘿嘿的聲音,他們走進電梯,電梯門合上後裏面壹陣大笑,大笑的聲音和電梯壹起下降,下降的笑聲裏還有咳嗽的聲音。
我是最後壹個離開的,當時他還跪在那裏,我想和他說幾句話,可是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麽。他看看我,臉上掛著苦笑,好像要說些什麽,結果什麽也沒說。他低下頭,把那束玫瑰放在地上,緊挨著自己的膝蓋。我覺得不應該繼續站在那裏,走進空無壹人的電梯,電梯下降時我的心情也在下降。
他第二天沒來公司上班,所以公司裏笑聲朗朗,全是有關他下跪求愛的話題,男男女女都說他們來上班時充滿好奇,電梯門打開時想看看他是否仍然跪在那裏。他沒有跪在那裏讓不少人感到惋惜,似乎生活壹下子失去不少樂趣。下午的時候他辭職了,來到公司樓下,給他熟悉的壹位同事打了壹個電話,這位同事拿著電話說:
“我正忙著呢。”
這位放下電話後,揮舞雙手大聲告訴大家:“他辭職了,他都不敢上來,要我幫忙整理他的物品送下去。”
壹陣笑聲之後,另壹位同事接到他的電話,這壹位大聲說:“我在忙,妳自己上來吧。”
這壹位放下電話還沒說是他打來的,笑聲再次轟然響起。我遲疑壹下後站了起來,走到他的辦公桌那裏,先將桌上的東西歸類,再將抽屜裏的物品取出來放在桌上,然後去找來壹個紙箱,將他的東西全部裝進去。這期間他給第三位同事打電話,我聽到第三位在電話裏告訴他:
“楊飛在整理妳的東西。”
我搬著紙箱走出寫字樓,他就站在那裏,壹副疲憊不堪的模樣,我把紙箱遞給他,他沒有正眼看我,接過紙箱說了壹聲謝謝,轉身離去。我看著他低頭穿過馬路,消失在陌生的人流裏,心裏湧上壹股難言的情緒,他在公司工作五年,可是對他來說公司裏的同事與大街上的陌生人沒有什麽兩樣。
我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坐下後,有幾個人走過來打聽他說了什麽,他是什麽表情。我沒有擡頭,看著電腦屏幕簡單地說:
“他接過紙箱就走了。”
這壹天,我們這個壹千多平米的辦公區域洋溢著歡樂的情緒,我來到這裏兩年多了,第壹次有這麽多人同時高興,他們回憶他昨天下跪的情景,又說起他以前的某些可笑事情,說他曾經在壹個公園散步時遭遇搶劫,兩個歹徒光天化日之下走到他面前,問他附近有警察嗎?他說沒有。歹徒再問他,真的沒有?他說,肯定沒有。然後兩把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,要他把錢包交出來……他們哈哈笑個不停,大概只有我壹個人沒有笑,後來我註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裏,不想去聽他們的說話。有兩次因為文件要復印,我起身時與她的目光不期而遇,她就坐在我的斜對面,我立刻扭過頭去,此後不再向那裏看去。後來有幾個男的走到她面前,討好地說:
“不管怎樣,為妳下跪還是值得的。”
我聽到她刻薄的回答:“妳們也想試試。”
在壹片哄笑裏,那幾個男的連聲說:“不敢,不敢……”
那壹刻我輕輕笑了,她說話從來都是友好的,第壹次聽到她的刻薄言辭,我覺得很愉快。
公司的年輕人裏面,我可能是唯壹沒有追求過她的,雖然心裏有時也會沖動,我知道這是暗戀,可是自卑讓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。我們的辦公桌相距很近,我從來沒有主動去和她說話,只是愉快地感受著她就在近旁的身影和聲息,這是隱藏在心裏的愉快,沒有人會知道,她也不會知道。她在公關部,我在營銷部,她偶爾會走過來問我幾個工作上的問題,我以正常的目光註視她,認真聽完她的話,做出自己的回答。我很享受這樣的時刻,可以大大方方欣賞她的美麗容貌。自從她用近乎冷酷的方式對待那位下跪的求愛者之後,不知為何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。可是她經常走過來問我工作上的事,比過去明顯增多,每次我都是低著頭回答。
幾天後我下班晚了壹點,她剛好從樓上管理層的辦公區域乘電梯下來,電梯門打開後我看見她壹個人在裏面,正在猶豫是否應該進去,她按住開門鍵說:
“進來呀。”
我走進電梯,這是第壹次和她單獨在壹起,她問我:“他怎麽樣?”
我先是壹楞,接著明白她是在問那個下跪求愛者,我說:“他看上去很累,可能在街上走了壹夜。”
我聽到她的深呼吸,她說:“他這樣做太讓我尷尬了。”
我說:“他也讓自己尷尬。”
我看著電梯下降時壹個壹個閃亮的樓層數字。
她突然問我:“妳是不是覺得我有點冷酷?”
我是覺得她有點冷酷,可是她聲音裏的孤獨讓我突然難過起來。我說:“我覺得妳很孤獨,妳好像沒有朋友。”
說完這話我的眼睛濕潤了。我不會在深夜時刻想到她,因為我壹直告誡自己,她是壹個和我沒有關系的人,可是那壹刻我突然為她難過了。她的手伸過來碰了碰我的手臂,我低頭看到她遞給我壹包紙巾,抽出壹張後還給她時沒有看她。
此後的日子我們像以前壹樣,各自上班和下班,她會經常走過來問我壹些工作上的事情,我仍然用正常的目光註視她,聽她說話,回答她的問題。除此之外,我們沒有其他的交往。雖然早晨上班在公司相遇時,她的眼睛裏會閃現壹絲欣喜的神色,可是電梯裏的小小經歷沒有讓我想入非非,我只是覺得這個經歷讓我們成為關系密切的同事。想到上班時可以見到她,我已經心滿意足,壹點也沒有意識到她開始鐘情於我。
那個時候的姑娘們都以嫁給領導的兒子為榮,她是壹個例外,她壹眼就能看出那幾個紈絝子弟是不能終身相伴的。她在跟隨公司總裁出席的商業晚宴上,見識了不少成功男人背著妻子追求別的女人時的殷勤言行,可能是這樣的經歷決定了她當時的擇偶標準,就是尋找壹個忠誠可靠的男人,我碰巧是這樣的人。
我在情感上的愚鈍就像是門窗緊閉的屋子,雖然愛情的腳步在屋前走過去又走過來,我也聽到了,可是我覺得那是路過的腳步,那是走向別人的腳步。直到有壹天,這個腳步停留在這裏,然後門鈴響了。
那是壹個春天的傍晚,公司裏空空蕩蕩,我因為有些事沒有做完正在加班工作,她走了過來。我聽到高跟鞋敲打大理石地面的聲音來到我的身旁,我擡起頭來時看到她的微笑。
“很奇怪,”她說,“我昨晚夢見和妳結婚了。”
我目瞪口呆,這怎麽可能呢?我當時壹句話也說不出來,她看著我,若有所思地說:
“真是奇怪。”
她說著轉身離去,高跟鞋敲打地面的聲音就像我的心跳壹樣咚咚直響,高跟鞋的聲音消失後,我的心跳還在咚咚響著。
我想入非非了,接下去的幾天裏魂不守舍,夜深人靜之時壹遍遍回想她說這話時的表情和語氣,小心翼翼地猜想她是否對我有意?日有所想夜有所思,有壹天晚上我夢見和她結婚了,不是熱鬧的婚禮場景,而是我們兩個人手拉手去街道辦事處登記結婚的情景。第二天在公司見到她的時候,我突然面紅耳赤。她敏銳地發現這壹點,趁著身旁沒人的時候,她問我:
“為什麽見到我臉紅?”
她的目光咄咄逼人,我躲開她的眼睛,膽戰心驚地說:“我昨晚夢見和妳去登記結婚。”
她莞爾壹笑,輕聲說:“下班後在公司對面的街上等我。”
這是如此漫長的壹天,幾乎和我的青春歲月壹樣長。我工作時思維渙散,與同事說話時答非所問,墻上的時鐘似乎越走越慢,讓我感到呼吸越來越困難。我苦苦熬過這拖拖拉拉的時間,終於等到了下班,可是當我站在公司對面的街上時,仍然呼吸困難,不知道她是在加班工作還是在故意拖延時間考驗我,我壹直等到天黑,才看見她出現在公司的大門口,她在臺階上停留片刻,四處張望,看到我以後跑下臺階,躲避著來往的汽車橫穿馬路跑到我面前,她笑著說:
“餓了吧?我請妳吃飯。”
說完她親熱地挽住我的手臂往前走去,仿佛我們不是初次約會,而是戀愛已久。我先是壹驚,接著馬上被幸福淹沒了。
接下去的幾天裏,我時常詢問自己這是真的,還是幻覺?我們約好每天早晨在壹個公交車站見面,然後壹起坐車去公司。我總是提前壹個多小時站在那裏,她沒有出現的時候我會忐忑不安,看見她甩動手臂快步向我走來的飄逸迷人身姿後,我才安心了,確定這不是幻覺,這是真的。
我們壹起上班壹起下班,十來天過去,公司裏的同事沒有註意到我們正在戀愛,他們可能和此前的我壹樣,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。有時下班後我的工作做完,她的還沒有做完,我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她。
有同事走過時問我:“怎麽還不走?”
我說:“我在等李青。”
我看見這位同事臉上神秘的笑容,似乎在笑我即將重蹈他人覆轍。另外的時候她的工作做完了,我的還沒有做完,她就坐到我身旁來。
走過的同事表情不壹樣了,滿臉驚訝地問她:“怎麽還不走?”
她回答:“我在等他。”
我們戀愛的消息在公司裏沸沸揚揚,男的百思不解,認為李青看不上市裏領導的兒子看上我是丟了西瓜撿芝麻。他們覺得自己壹點也不比我差,為此有些憤憤不平,私下裏說,鮮花插在牛糞上是真的,癩蛤蟆吃到天鵝肉也是真的。女的幸災樂禍,她們見到我時笑得意味深長,然後互相忠告,找對象不要太挑剔,差不多就行了,看看人家李青,挑來挑去結果挑了壹個便宜貨。
我們沈浸在自己的愛情裏,那些針對我們的議論,用她的話說只是風吹草動。她也有氣憤的時候,當她知道他們說我是牛糞、癩蛤蟆和便宜貨時,她說粗話了,說他們是在放屁。
她凝視我的臉說:“妳很帥。”
我自卑地說:“我確實是便宜貨。”
“不,”她說,“妳善良,忠誠,可靠。”
我們手拉手走在夜色裏的街道上,然後長時間坐在公園僻靜之處的椅子上,她累了就會把頭靠在我肩上,我伸手摟住她的肩膀。就是在那裏,我第壹次吻了她,她第壹次吻了我。後來我們經常坐在她租住的小屋裏,她向我敞開自己柔弱的壹面,講述跟隨公司總裁參加各個洽談生意晚宴時的艱難,那些成功男人好色的眼神和下流的言辭,她心裏厭惡他們,仍然笑臉相迎與他們不斷幹杯,然後去衛生間嘔吐,嘔吐之後繼續與他們幹杯。她與市裏領導兒子的戀愛只是傳言,她只見過三個,都是公司總裁介紹的,那三個有著不同的公子哥派頭,第壹個說話趾高氣揚,第二個總是陰陽怪氣看著她,第三個剛見面就對她動手動腳,她微笑著抵抗他,他說妳別裝了。她的父母遠在異鄉,她在遭遇各式各樣的委屈之後就會給他們打電話,她想哭訴,可是電話接通後她強作歡笑,告訴父母她壹切都很好,讓他們放心。
她的講述讓我心疼,我雙手捧住她的臉,親吻她的眼睛,把她弄得癢癢的,她笑了。她說很早就註意到我,發現我是壹個勤奮工作的人,而壹個遊手好閑的同事總是將我的業績據為己有,拿去向上面匯報,我卻從不與他計較。我告訴她,有幾次我確實很生氣,要去質問他,可是話到嘴邊又說不出來。
我說:“有時我也恨自己的軟弱。”
她愛憐地摸著我的臉說:“妳不會對我很強硬吧?”
“絕對不會。”
她繼續說,當公司裏的年輕男人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她時,我似乎對她無動於衷,她有些好奇,就過來詢問壹些工作上的事,觀察我的眼睛,可是我的眼神和公司裏其他男人看著她的眼神不壹樣,只是單純的友好眼神。後來發生的那個下跪求愛者的事情讓她對我有了好感,她悄悄看著我在大家的哄笑聲裏替那個人整理物品送了下去。她停頓了壹下,聲音很輕地說自己在外面越是風頭十足,晚上回到租住的小屋越是寂寞孤單,那個時刻她很想有壹個相愛的人陪伴在身旁。當我和她在電梯裏短暫相處,我眼睛濕潤的那壹刻,她突然感受到被人心疼的溫暖,後來的幾天裏她越來越覺得我就是那個可以陪伴在身旁的人。
然後她輕輕捏住我的鼻子,問我:“為什麽不追我?”
我說:“我沒有這個野心。”
壹年以後,我們結婚了。我父親的宿舍太小,我們租了那套壹居室的房子作為新房。我父親喜氣洋洋,因為我娶了這麽壹個漂亮聰明的姑娘。她對我父親也很好,周末的時候接他過來住上壹天,每次都是我們兩個人去接,擠上公交車以後她總能敏捷地為我父親搶到壹個座位,這讓我想起第壹次見到她的情景,我笑了,但是從來沒有告訴她這個。春節的時候,我們坐上火車去看望她的父母,她父母都是壹家國營工廠裏的工人,他們樸實善良,很高興女兒嫁給壹個可靠踏實的男人。
我們婚後的生活平靜美好,只是她仍然要跟隨公司總裁出去應酬,天黑之後我獨自在家等候,她常常很晚回家,疲憊不堪地開門進屋,滿身酒氣地張開雙臂要我抱住她,將頭靠在我的胸前休息壹會兒才躺到床上去。她厭倦這些應酬,可是又不能推掉應酬,那時她已是公關部的副經理。她看不上這個副經理的職位,用她的話說只是陪人喝酒的副經理。她曾經對我說過,美麗是女人的通行證,可是這張通行證壹直在給公司使用,自己壹次也沒有用過。
我們在自己生活的軌道上穩步前行了兩年多,開始計劃買壹套屬於自己的房子,同時決定要壹個孩子,她覺得有了孩子也就有了推掉那些應酬的理由。她為此停止服用避孕藥,可是這時候我們前行的軌道上出現了障礙物。壹次出差的經歷讓她真正意識到自己是什麽樣的人,也意識到我是什麽樣的人。她是壹個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人,而我只會在自己的命運裏隨波逐流。
她坐在飛機上,身旁是壹個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博士,這個男人剛剛自己創業,比她大十歲,有妻子有孩子,兩個多小時的飛行期間,他滿懷激情地向她描述了自己事業的遠大前程。我想是她的美貌吸引了他,所以他滔滔不絕地說了那麽多話。她跟隨我們公司的總裁參加過很多商業談判的晚宴,這樣的經驗讓她可以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議。他在迷戀她的美貌之後,開始驚嘆她的細致和敏銳,在飛機上就向她發出邀請:
“和我壹起幹吧。”
下了飛機,他沒有住到自己預訂的賓館,而是搬到她住的賓館,表示要繼續向她請教,他的理由冠冕堂皇,可是我覺得他更多的仍然是貪圖她的美色。白天兩個人分別工作,晚上坐在賓館的酒吧裏討論他創業中遇到的困難,她繼續給他提供建議。她不僅為他的事業提供新的設想,還告訴他在中國做事的很多規矩,比如如何和政府部門裏的官員打交道,如何給他們壹些好處。他在美國留學生活很多年,不太了解中國現實中的諸多潛規則。兩個人分手時,他再次提出和她壹起幹的願望。她笑而不答,給他留下家裏的電話號碼。
那個時候她心裏出現了變化。我們公司的總裁只是認為她漂亮聰明,並不知道她的才幹和野心,她覺得飛機上相遇的這個男人能夠真正了解自己。
她回家後重新服用避孕藥,她說暫時不想要孩子。然後每個晚上都有電話打進來,她拿著電話與他交談,有時候壹個多小時,有時候兩三個小時。剛開始常常是我去接電話,後來電話鈴聲響起後我不再去接。她在電話裏說的都是他公司業務上的事,他詢問她,她思考後回答他。後來她拿著電話聽他說話,自己卻很少說話。她放下電話就會陷入沈思,片刻後才意識到我坐在壹旁,努力讓自己微笑壹下。我預感到他們之間談話的內容發生了變化,我什麽都不說,但是心裏湧上了陣陣悲哀。
半年後他來到我們這個城市,那時候他已經辦好離婚手續。她吃過晚飯去了他所住的賓館,她出門前告訴我,是去他那裏。我在沙發上坐了壹個晚上,腦子裏壹片空白,裏面的思維似乎死去了。天亮的時候她才回家,以為我睡著了,小心翼翼地開門,看到我坐在沙發上,她不由怔了壹下,隨後有些膽怯地走過來,在我身旁坐下。
她從來都是那麽地自信,我這是第壹次見到她的膽怯。她不安地低著頭,聲音發顫地告訴我,那個人離婚了,是為她離婚的,她覺得自己應該和他在壹起,因為她和他誌同道合。我沒有說話。她再次說他是為她離婚的,我聽到了強調的語氣,我心想任何壹個男人都願意為她離婚。我仍然沒有說話,但是知道自己已經失去她了。我明白她和我在壹起只能過安逸平庸的生活,和他在壹起可以開創壹番事業。其實半年前我就隱約預感她會離我而去,半年來這樣的預感越來越強烈,那壹刻預感成為了事實。
她深深吸了壹口氣,對我說:“我們離婚吧。”
“好吧。”我說。
我說完忍不住流下眼淚,雖然我不願意和她分手,可是我沒有能力留住她。她擡起頭來看到我在哭泣,她也哭了,她用手抹著眼淚說:
“對不起,對不起……”
我擦著眼睛說:“不要說對不起。”
這天上午,我們兩個像往常那樣壹起去了公司。我請了壹天的事假,她遞交了辭職報告,然後我們去街道辦事處辦理了離婚手續。她先回家整理行李,我去銀行把我們兩個人共同的存款全部取了出來,有六萬多元,這是準備買房的錢。回家後我把錢交給她,她遲疑壹下,只拿了兩萬元。我搖搖頭,要她把錢都拿走。她說兩萬元足夠了。我說這樣我會擔心的。她低著頭說我不用擔心,我應該知道她的能力,她會應付好壹切的。她把兩萬元放進提包裏,剩下的四萬多元放在桌子上。然後她深情地註視起我們共同生活的屋子,她對屋子說:
“我要走了。”
我幫助她收拾衣物,裝滿了兩個大行李箱。我提著兩個箱子送她到樓下的街道上,我知道她會先去他所住的賓館,然後他們兩個壹起去機場,我為她叫了壹輛出租車,把兩個箱子放進後備箱。分別的時刻來到了,我向她揮了揮手,她上來緊緊抱住我,對我說:
“我仍然愛妳。”
我說:“我永遠愛妳。”
她哭了,她說:“我會給妳寫信打電話。”
“不要寫信也不要打電話,”我說,“我會難受的。”
她坐進出租車,出租車駛去時她沒有看我,而是擦著自己的眼淚。她就這樣走了,走上她命中註定的人生道路。
我的突然離婚對我父親是壹個晴天霹靂,他壹臉驚嚇地看著我,我簡單地告訴他我們離婚的原因。我說和她結婚本來就是壹場誤會,因為我配不上她。我父親連連搖頭,不能接受我的話。他傷心地說:
“我壹直以為她是壹個好姑娘,我看錯人了。”
我父親的同事郝強生和李月珍夫婦,壹直以來把我當成他們自己的孩子,他們知道這個消息也是同樣震驚。郝強生壹口咬定那個男的是個騙子,以後會壹腳把她蹬了,說她不知好歹,說她以後肯定會後悔的。李月珍曾經是那麽地喜歡她,說她聰明、漂亮、善解人意,現在認定她是壹個勢利眼,然後感嘆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裏,勢利的女人越來越多。李月珍安慰我,說這世上比她好的姑娘有的是,說她手裏就有壹把。李月珍給我介紹了不少姑娘,都沒有成功。原因主要在我這裏,我和她共同生活的日子裏,她悄無聲息地改造了我,她在我心裏舉世無雙。在和那些姑娘約會的時候,我總是忍不住將她們和她比較,然後在失望裏不能自拔。
後來的歲月裏,我有時候會在電視上看到她接受采訪,有時候會在報紙和雜誌上看到有關她的報道。她讓我既熟悉又陌生,熟悉的是她的笑容和舉止,陌生的是她說話的內容和語調。我感到她似乎是那家公司的主角,她的丈夫只是配角。我為她高興,電視和報紙雜誌上的她仍然是那麽美麗,這張通行證終於是她自己在使用了。然後我為自己哀傷,她和我壹起生活的三年,是她人生中的壹段歪路,她離開我以後才算走上了正路。
在消失般的幽靜裏,我再次聽到那個陌生女人的呼喚聲:“楊飛——”
我睜開眼睛環顧四周,雨雪稀少了,壹個很像是李青的女人從左邊向我走來,她身穿壹件睡袍,走來時睡袍往下滴著水珠。她走到我面前,仔細看了壹會兒我的臉,又仔細看了壹會兒我身上的睡衣,她看見已經褪色的“李青”兩字。然後詢問似的叫了壹聲:
“楊飛?”
我覺得她就是李青,可是她的聲音為何如此陌生?我坐在長椅裏無聲地看著她,她臉上出現奇怪的神色,她說:
“妳穿著楊飛的睡衣,妳是誰?”
“我是楊飛。”我說。
她疑惑地望著我離奇的臉,她說:“妳不像是楊飛。”
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臉,左眼在顴骨那裏,鼻子在鼻子的旁邊,下巴在下巴的下面。
我說:“我忘記整容了。”
她的雙手伸過來,小心翼翼地把我掉在外面的眼珠放回眼眶裏,把我橫在旁邊的鼻子移到原來的位置,把我掛在下面的下巴哢嚓壹聲推了上去。
然後她後退壹步仔細看著我,她說:“妳現在像楊飛了。”
“我就是楊飛,”我說,“妳像李青。”
“我就是李青。”
我們同時微笑了,熟悉的笑容讓我們彼此相認。
我說:“妳是李青。”
她說:“妳確實是楊飛。”
我說:“妳的聲音變了。”
“妳的聲音也變了。”她說。
我們互相看著。
“妳現在的聲音像是壹個我不認識的人。”我說。
“妳的聲音也像是壹個陌生人。”她說。
“真是奇怪,”我說,“我是那麽熟悉妳的聲音,甚至熟悉妳的呼吸。”
“我也覺得奇怪,我應該熟悉妳的聲音……”她停頓壹下後笑了,“也熟悉妳的呼嚕。”
她的身體傾斜過來,她的手撫摸起我的睡衣,摸到了領子這裏。
她說:“領子還沒有磨破。”
我說:“妳走後我沒有穿過。”
“現在穿上了?”
“現在是殮衣。”
“殮衣?”她有些不解。
我問她:“妳那件呢?”
“我也沒再穿過,”她說,“不知道放在哪裏。”
“妳不應該再穿。”我說,“上面繡有我的名字。”
“是的,”她說,“我和他結婚了。”
我點點頭。
“我有點後悔,”她臉上出現了調皮的笑容,她說,“我應該穿上它,看看他是什麽反應。”
然後她憂傷起來,她說:“楊飛,我是來向妳告別的。”
我看到她身上的睡袍還在滴著水珠,問她:“妳就是穿著這件睡袍躺在浴缸裏的?”
她眼睛裏閃爍出了我熟悉的神色,她問:“妳知道我的事?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什麽時候知道的?”
“昨天,”我想了壹下,“可能是前天。”
她仔細看著我,意識到了什麽,她說:“妳也死了?”
“是的,”我說,“我死了。”
她憂傷地看著我,我也憂傷地看著她。
“妳的眼神像是在悼念我。”她說。
“我也有這樣的感覺,”我說,“我們好像同時在悼念對方。”
她迷惘地環顧四周,問我:“這是什麽地方?”
我指指雨雪後面的那幢朦朧顯現的陳舊樓房,她定睛看了壹會兒,想起來曾經記錄過我們點滴生活的那套壹居室。
她問我:“妳還住在那裏?”
我搖搖頭說:“妳走後我就搬出去了。”
“搬到妳父親那裏?”
我點點頭。
“我知道為什麽走到這裏。”她笑了。
“在冥冥之中,”我說,“我們不約而同來到這裏。”
“現在誰住在那套房子裏?”
“不知道。”
她的眼睛離開那幢樓房,雙手裹緊還在滴水的睡袍說:“我累了,我走了很遠的路來到這裏。”
我說:“我沒走很遠的路,也覺得很累。”
她的身體再次傾斜過來,坐到長椅上,坐在我的左邊。她感覺到了搖搖欲墜,她說:“這椅子像是要塌了。”
我說:“過壹會兒就好了。”
她小心翼翼地坐著,身體繃緊了,片刻後她的身體放松下來,她說:“不會塌了。”
我說:“好像坐在壹塊石頭上。”
“是的。”她說。
我們安靜地坐在壹起,像是坐在睡夢裏。似乎過去了很長時間,她的聲音蘇醒過來。
她問我:“妳是怎麽過來的?”
“我不知道,”我想起了自己的最後情景,“我在壹家餐館裏吃完壹碗面條,桌子上有壹張報紙,看到關於妳的報道,餐館的廚房好像著火了,很多人往外逃,我沒有動,壹直在讀報紙上妳自殺的消息,接著壹聲很響的爆炸,後來發生的事就不知道了。”
“就是在昨天?”她問。
“也可能是前天。”我說。
“是我害死妳的。”她說。
“不是妳,”我說,“是那張報紙。”
她的頭靠在我的肩膀上:“可以讓我靠壹下嗎?”
我說:“妳已經靠在上面了。”
她好像笑了,她的頭在我肩上輕微顫動了兩下。她看見我左臂上戴著的黑布,伸手撫摸起來。
她問我:“這是為我戴的嗎?”
“為我自己戴的。”
“沒有人為妳戴黑紗?”
“沒有。”
“妳父親呢?”
“他走了,壹年多前就走了。他病得很重,知道治不好了,為了不拖累我,悄悄走了。我到處去找,沒有找到他。”
“他是壹個好父親,他對我也很好。”她說。
“最好的父親。”我說。
“妳妻子呢?”
我沒有說話。
“妳有孩子嗎?”
“沒有,”我說,“我後來沒再結婚。”
“為什麽不結婚?”
“不想結婚。”
“是不是我讓妳傷心了?”
“不是,”我說,“因為我沒再遇到像妳這樣的女人。”
“對不起。”
她的手壹直撫摸我左臂上的黑布,我感受到她的綿綿情意。
我問她:“妳有孩子嗎?”
“曾經想生壹個孩子,”她說,“後來放棄了。”
“為什麽?”
“我得了性病,是他傳染給我的。”
我感到眼角出現了水珠,是雨水和雪花之外的水珠,我伸出右手去擦掉這些水珠。
她問我:“妳哭了?”
“好像是。”
“是為我哭了?”
“可能是。”
“他在外面包二奶,還經常去夜總會找小姐,我得了性病後就和他分居了。”她嘆息壹聲,繼續說,“妳知道嗎?我在夜裏會想起妳。”
“和他分居以後?”
“是的,”她遲疑壹下說,“和別的男人完事以後。”
“妳愛上別的男人了?”
“沒有愛,”她說,“是壹個官員,他完事走後,我就會想起妳。”
我苦笑壹下。
“妳吃醋了?”
“我們很久以前就離婚了。”
“他走後,我壹個人躺在床上很長時間想妳。”她輕聲說,“我們在壹起的時候,我經常要去應酬,再晚妳也不會睡,壹直等我,我回家時很累,要妳抱住我,我靠在妳身上覺得輕松了……”
我的眼角又出現了水珠,我的右手再去擦掉它們。
她問我:“妳想我嗎?”
“我壹直在努力忘記妳。”
“忘記了嗎?”
“沒有完全忘記。”
“我知道妳不會忘記的,”她說,“他可能會完全忘記我。”
我問她:“他現在呢?”
“逃到澳洲去了。”她說,“剛有風聲要調查我們公司,他就逃跑了,事先都沒告訴我。”
我搖了搖頭,我說:“他不像是妳的丈夫。”
她輕輕笑了,她說:“我結婚兩次,丈夫只有壹個,就是妳。”
我的右手又舉到眼睛上擦了壹下。
“妳又哭了?”她說。
“我是高興。”我說。
她說起了自己的最後情景:“我躺在浴缸裏,聽到來抓我的人在大門外兇狠地踢著大門,喊叫我的名字,跟強盜壹樣。我看著血在水中像魚壹樣遊動,慢慢擴散,水變得越來越紅……妳知道嗎?最後那個時刻我壹直在想妳,在想我們壹起生活過的那套很小的房子。”
我說:“所以妳來了。”
“是的,”她說,“我走了很遠的路。”
她的頭離開了我的肩膀,問我:“還住在妳父親那裏?”
我說:“那房子賣了,為了籌錢給我父親治病。”
她問:“現在住在哪裏?”
“住在壹間出租屋裏。”
“帶我去妳的出租屋。”
“那屋子又小又破,而且很臟。”
“我不在乎。”
“妳會不舒服的。”
“我很累,我想在壹張床上躺下來。”
“好吧。”
我們同時站了起來,剛才已經稀少的雨雪重新密集地紛紛揚揚了。她挽住我的手臂,仿佛又壹次戀愛開始了。我們親密無間地走在虛無縹緲的路上,不知道走了有多長時間,來到我的出租屋,我開門時,她看見門上貼著兩張要我去繳納水費和電費的紙條,我聽到她的嘆息,我問她:
“為什麽嘆氣?”
她說:“妳還欠了水費和電費。”
我把兩張紙條撕下來說:“我已經繳費了。”
我們走進這間雜亂的小屋。她似乎沒有註意到屋子的雜亂,在床上躺了下來,我坐在床旁的壹把椅子裏。她躺下後睡袍敞開了,她和睡袍都是疲憊的模樣。她閉上眼睛,身體似乎漂浮在床上。過了壹會兒,她的眼睛睜開來。
她問:“妳為什麽坐著?”
我說:“我在看妳。”
“妳躺上來。”
“我坐著很好。”
“上來吧。”
“我還是坐著吧。”
“為什麽?”
“我有點不好意思。”
她坐了起來,壹只手伸向我,我把自己的手給了她,她把我拉到了床上。我們兩個並排仰躺在那裏,我們手糾纏在壹起,我聽到她勻稱的呼吸聲,恍若平靜湖面上微波在蕩漾。過了壹會兒,她輕聲說話,我也開始說話。我心裏再次湧上奇怪的感覺,我知道自己和壹個熟悉的女人躺在壹起,可是她說話的陌生聲音讓我覺得是和壹位素不相識的女人躺在壹起。我把這樣的感覺告訴她,她說她也有這樣的奇怪感覺,她正和壹個陌生男人躺在壹起。
“這樣吧,”她的身體轉了過來,“讓我們互相看著。”
我的身體也轉過去看著她,她問我:“現在好些了嗎?”
“現在好些了。”我說。
她濕漉漉的手撫摸起了我受傷的臉,她說:“我們分手那天,妳把我送上出租車的時候,我抱住妳說了壹句話,妳還記得嗎?”
“記得,”我說,“妳說妳仍然愛我。”
“是這句話。”她點點頭,“妳也說了壹句話。”
“我說我永遠愛妳。”
她和睡袍壹起爬到了我的身上,我有些不知所措,雙手舉了起來,不敢去抱她。她的嘴巴對準我的耳朵濕漉漉地說:
“我的性病治好了。”
“我不是這個意思。”
“抱住我。”
我的雙手抱住了她。
“撫摸我。”
我的雙手撫摸起了她的背部、腰部和大腿,我撫摸了她的全身。她的身體濕漉漉的,我的手似乎是在水中撫摸她的身體。
我說:“妳比過去胖了。”
她輕輕笑了:“是腰胖了。”
我的手流連忘返地撫摸她,然後是我的身體撫摸起了她的身體,她的身體也撫摸起了我的身體,我們的身體仿佛出現了連接的紐帶……我在床上坐了起來,看到她站在床邊,正在用手整理自己的頭發。
她對我說:“妳醒來了。”
“我沒有睡著。”
“我聽到妳打呼嚕了。”
“我確實沒有睡著。”
“好吧,”她說,“妳沒有睡著。”
她系上了睡袍的腰帶,對我說:“我要走了,幾個朋友為我籌備了盛大的葬禮,我要馬上趕回去。”
我點點頭,她走到門口,打開屋門時回頭看著我,惆悵地說:“楊飛,我走了。”